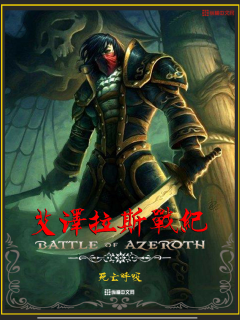开出龙骨港之后,我们可爱的图拉扬小哥哥就开始呕吐。虽然法奥大主教给他各种治疗,甚至连圣光都用上了,但收效甚微。
从此他开启了昏睡模式。偶尔出现在船的甲板上也会把吃进去但没有消化完全的食物贡献给海里的鱼虾们。
在船上漂泊是件枯燥的事,或许风和日丽会稍微好些,但一直的阴雨绵绵让人更加压抑,那无边大海和滚滚的海浪总让我提心吊胆。
船行两天后终于迎来了艳阳高照。几乎所有人都来到了甲板上。
库尔提拉斯是个像暴风王国一样远离大陆的王国,但比暴风王国有一点好,就是离着大陆并不很远。我们乘坐的这艘船是库尔提拉斯之王海军统帅戴林·普罗德摩尔委派艾什凡大公前来迎接的。
出发四天后终于看到了陆地。船长指着前面说:“咱们得快点了!要赶到日落之前到达潮汐之谷,之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明早一早我们必须到达伯拉勒斯港的码头,要是耽误了时间咱们会被大潮冲回来。”
“怎么回事?”好奇宝宝已经习惯了这种摇晃,而且他现在心情好极了。
“伯拉勒斯港的位置很特殊,他是库尔提拉斯王国的中心。”船长说道:“库尔提拉斯王国由三片大陆和一座岛组成。伯拉勒斯港就在三片大陆的中心。”
“据说伯拉勒斯是潮汐之神的杰作。”他拿手指着前方。“那里……是个喇叭形状的海峡,但那里的水流很奇怪,洋流每天到了晚上涨潮的时候往里灌,但是第二天早晨退潮的时候巨大的暗流从水下冲向我们这个地方。白天往外流,晚上往里流。没人知道这水是怎么回事,没人说得清。如果不在码头停靠,即使下了锚也会被海潮带跑,潮汐之谷的水下也有很多沉船,都是被海潮带走的结果。”
船帆收起来一半,在进入海峡前只留下了最后一片帆,船缓缓驶入了潮汐之谷。
两岸悬崖的崖顶上诸多的堡垒预示着想从这里进攻伯拉勒斯要付出的代价会非比寻常。
“感受到了么?船变快了。”船长说。
“似乎没什么风了。”
“峡谷的风很怪,有时候往里吹,有时候往外吹。”他说:“春天时候,早晚往里吹,到中午一般就没什么风了,一直持续到黄昏。夏天时候,从早晨开始往里吹,到黄昏就会变风向开始往外。”
我觉得这是胡说八道。“那秋天呢?”
“秋天的风白天晚上都往里吹,冬天没什么规律。”他说。
我看着他一脸的不敢相信。他则哈哈大笑没再继续说下去。
晚上十点多船队终于稳稳停靠在了伯拉勒斯港的港口码头上。码头上灯火通明,无数火把火盆火堆将码头照亮。
码头上站着很多人,可以说非常多。这个时间早该是进入甜美梦乡的时候,却有如此多的人在这里等待着迎接我们的到来。真不知是真心想提前见见宗教的面貌,还是因为国王的命令而不得不服从。
我们提前把脸收拾干净将衣服整理得整整齐齐。大主教更是换上了他的金色镶边袍服。
船梯靠了过来,我站在船边往下俯瞰,统帅真的来了!号角吹了起来,周围也响起了音乐。这迎接仪式整得是真像样。
码头上众人高呼万岁,赞美着圣光。
看着他们模糊的脸我心里一阵打鼓,究竟真心赞美的不知道有多少,因为耽误睡觉而咒骂的估计应该不在少数。
从码头到统帅城堡这一路布置得灯火辉煌。对大主教到来的重视可见一斑。
到库尔提拉斯之前和到那里之后我的自身感受是不同的。从开进海峡开始我就觉得心里老是有点不大舒服,一阵阵的心悸,即便是什么都没做还是会一阵阵的心悸。然后就是左臂一阵阵的发麻。
白天还好一些,可是到了夜里睡觉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会让我直接从睡眠中醒来。
我只向乌瑟尔说过这事,这段时间法奥大主教很辛苦我知道,所以我只找了乌瑟尔。他也带我去找了随军的御医可并没任何用处。这种心悸的感觉越来越重,甚至吃饭的时候都会因为心悸而毫无食欲,更别说睡觉了。
我捏着发麻的左手,草药没有用,御医给我放了血也没有用,最后乌瑟尔给我施以圣光术的时候我直接晕了过去。
那天之后我就独自找个地方待着,不给他们添麻烦,毕竟他们都很忙。
离开国王堡垒到外面走走是乌瑟尔给我搞到的最好的待遇了。穿着洛丹伦圣光教会的法袍走在大街上的时候频频引来注视的目光。
有羡慕,有崇拜,有不屑,也有敌意。
前两种人的目光让我比较受用,我觉得受他们的这份尊敬着实是有点受之有愧,然而另外两种则有点让我不解。直到我看到那些穿着异样法袍的家伙朝我投来的目光我才有所察觉。
原本我以为人类世界只有一种宗教,就是圣光教派,可那天我才知道也是有其他信仰教派的。那些异教徒身上的长袍唯一统一的是土黄色跟海蓝色相间。而这种长袍上打满了补丁,看上去就跟乞丐没有很大的区别。另外就是这些家伙领口处镶嵌的一枚眼睛状的石头坠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他们宽大的罩帽遮住了他们大半张脸,偶尔露出的表情尤其是眼神叫我感觉十分阴郁。
我穿这身走到哪都是焦点,所以我很自觉地回到了国王城堡。可是很不巧的我在国王城堡里竟然又遇上了这些人,这些人从城堡里走出来,因为看不到脸所以我不知道他们的表情。可看到法奥大主教乌瑟尔和图拉扬的表情后我隐约感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这晚的宴会热闹非凡,昨天还没见踪影的达拉然法师们现在已经列席其中。
只是席上坐着的三个人里有两位我看着是如此的眼熟。戴林统帅向在座的各位隆重介绍了三位,中间那位就是曾在洛丹伦的庆典上注视过的那个老头,他叫安东尼达斯,达拉然的最高领袖,达拉然首席大魔法,大魔导师。
安东尼达斯右边的家伙是达拉然著名魔法师,魔导师德伦登,我不认识这个人仅仅记住了这个名字。另外有个人我跟他也有过一面之缘你们还记得么?
克尔苏加德。
这些人的眼睛里带着一丝友善,可更多的是那种如天神般的无上的威严。这种从内到外不自觉释放出来的压力是绝对假装不了的。
权利会给人增加这种威严,另一个则是绝对的力量。
三个人的到来并没有给这个宴会带来沉闷反而更加活跃。
库尔提拉斯这群粗犷的胖子们也有着活泼的一面。弄臣竭尽全力的逗笑惹得满堂大笑。舞蹈表演也叫我看到了这群身材高挑的库尔提拉斯少女们柔美的一面。她们花白的大腿在灯火的映照下甚是好看。
宴会大厅里灯火通明,大厅正中间的墙壁上挂着四面巨大的家族旗帜。最左边是一面蓝色的带着眼睛的旗帜,然后是我见到的那个天秤的旗帜,然后是库尔提拉斯的船锚旗帜,最右边的则是一只海鹰。
旗帜下面的主席台上坐着四男四女八位大人。
库尔提拉斯船锚旗帜下的是统帅本人,跟统帅坐得很近的女人应该就是他夫人。这个面容姣好微微有点婴儿肥的女人脸上紧凑的五官很是端正,虽说看上去并不觉得很惊艳但很耐看。尤其是她一头的银丝像大海的浪花那样闪着银光。
左边天秤旗下的那对夫妻跟另外两对夫妻不同,那份高高在上的感觉甚至是戴林统帅都没有的。我记得这个家族徽记,艾什凡家族么!
统帅夫人身边的丰腴女士应该就是艾什凡家的女主人,她是一头黑发,黑色蕾丝的礼服几乎包裹不住傲人的胸脯,深色的眼影下一双杏眼看别人的眼神是高傲,但朝我们这边瞥过来的时候那感觉我不会形容。这个女人对性生活要求应该不低。那丰满的嘴唇是性欲和征服欲的象征。
这女人身上的珠宝令人咋舌,她双峰之间那颗巨大的宝石被光一打,反射出来的光都很是扎眼。
两个女人正在谈笑风生,她们俩眼睛不时往我们这边瞟来。不过自然不是看我,那眼神我不会形容,那种打量中带着一点调侃,渴望中又带着一丝戏谑,挑选又带着挑逗。
挑选妓女的男人会有这种眼神,但如果你见过女主人们挑选玩乐用的种人,这种眼神你会记一辈子。
我见过。哈哈!
艾什凡女士边上是她的男人,家族男主人,但这个男人虽然也有点神气但完全压不住艾什凡女士的锋芒。
艾什凡勋爵旁边的夫妻背后的旗帜上有一只蓝色的眼睛。那对夫妻严肃的表情上真叫我受不了。长得丑是一方面,这表情就跟死了妈一样。只是这个女人脖子里那个眼球状的宝石也是非常扎眼。
戴林统帅身边的男人表情就放松得多,这对夫妻身后的旗帜是一只猎鹰。女主人的脸竟然带着一丝青涩,她是这几个人里年龄最小的,大概比图拉扬大不了几岁,很清秀的样子,长长的睫毛低垂着,不知是害羞还是怎么。而她身边的那位大腹便便的勋爵喝酒喝的胡子上全是啤酒沫子。好白菜和猪的谚语出现在我脑海里。
介绍完主要嘉宾饮宴便正式开始。可没过多久图拉扬身边再次被几个女孩和女人们包围。继续站在他身边简直对我而言就是莫大大的羞辱。
站在窗边我打量着宴会厅的每一个人,直到身边出现一个上来搭讪我的女孩。
她只是一个女仆,但这个女孩显然跟任何一个女仆都不一样。不管是她的言语还是呻吟的声音都显示着她强烈的欲望。
出卖身体的人能出卖的也仅剩下这副肉体。而出卖的目的都是为了回报。有人是为了钱,有人是为了权,有人是为了地位,但她不同。
她温柔却并不十分柔软的小手按在我的胸口上轻声告诉我:“我听得到你的心跳……而我也听到了你胸膛里的另一个声音。”
这句话我记到现在。
这个女人在挑逗和满足之间施展的把戏现在看来很是拙劣,但对当时的我却很受用。
你们这群菜鸟里估计从未尝试过那温柔且热烈的温泉所以就不要幻想了。这方面的经验靠实践,理论只能用来吹牛逼。
“被我说中了……”那女孩的手抚触我的感觉现在都还记得清清楚楚,那种酥麻感跟深入接触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能够被你挂念,想必她一定是个温柔美丽的女子吧。”
这个女孩的话放到现在如果对我说,我内心会毫无波澜,但当时却很有触动。
“你很喜欢打听别人的事情。”我当时就这么说的。
“不。”她的话语里面带着一丝幽怨。“只是嫉妒。”
她略带痛苦却让自己努力去承受的表情让我感觉……很另类,但很刺激。
那表情不仅仅是痛,还带着些嫉妒和埋怨,有不满,有抗争,是难过,是不平,是绝望,是不甘,是在痛苦中寻求这延迟的快乐。
这种精神和肉体的痛苦之后带来的刺激让随后的高潮变得无与伦比。
很新奇的体验。
她从床上爬起来走到窗前,月光依然皎洁照在她微微有些丰腴的身体上。她的皮肤并不白,在银色的月光下也似乎没什么反光,只不过那光把她的身材照得竟然很有美感。
她捡起了地上的衣服背对着我,“用不了两天,你就会忘了我吧……”
那声音带着哀伤,语气里满是无奈。
“不会……”
我话还没说完,她已经套上了裙子走向了房门。
“你身上的光芒照亮过我。”她说完回眸的瞬间我似乎看到了一些晶莹的东西。
“谢谢你。”她又朝我行礼后就离开了房间。
我追上去想问她的名字,但她已经消失在了昏暗的走廊。